雙桂法脈,燈傳無盡——評《雙桂禪燈錄》
編輯導讀:
燈錄之體,肇于《祖堂集》而全于《景德傳燈錄》。其始于宋代禪門,脫胎于隋唐時期經傳記。作為外來宗教,佛教在與中土的儒道相論辯適應的過程中,產生了各具宗旨的宗派。經傳記雖是記錄某一佛經傳習源流的佛教史書,而其所包含的支派別行、諸師序集、感應事跡等內容, 亦在后來燈錄中有所體現,可視為其權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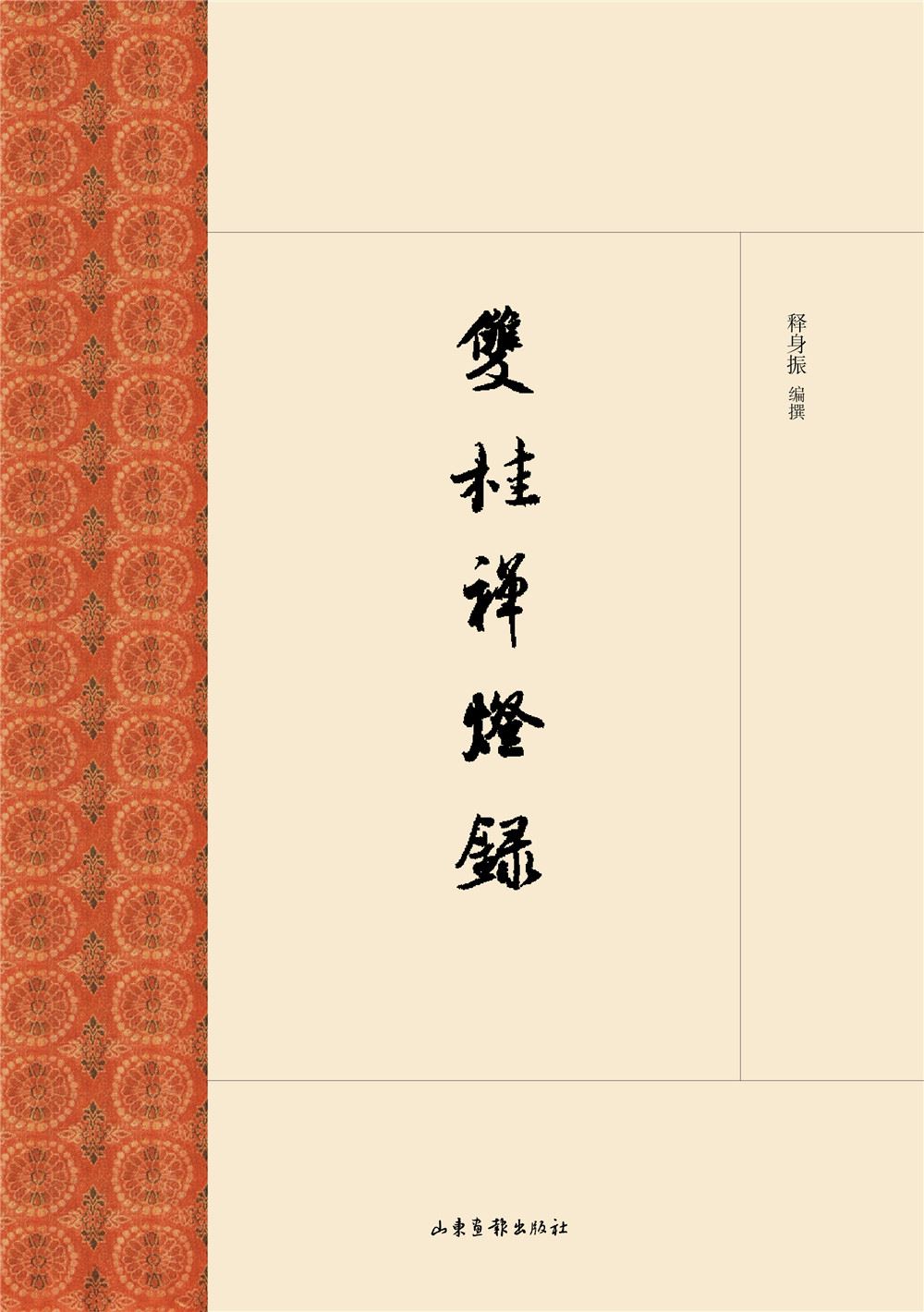
燈錄之體,肇于《祖堂集》而全于《景德傳燈錄》。其始于宋代禪門,脫胎于隋唐時期經傳記。作為外來宗教,佛教在與中土的儒道相論辯適應的過程中,產生了各具宗旨的宗派。經傳記雖是記錄某一佛經傳習源流的佛教史書,而其所包含的支派別行、諸師序集、感應事跡等內容, 亦在后來燈錄中有所體現,可視為其權輿。
與僧傳相比, 燈錄偏重于記言, 除敘傳主的生卒、師承、世壽、僧臘、謚、塔以外,主要部分是機緣語錄和贊、偈、箴、詩、歌等文字材料。其以傳承法脈編排而逐漸將受法機緣內化其中,易于讀者全面了解一人至一宗一派的歷史脈絡,從而明其道統,保證了佛法的完整和純正。燈錄有通史性質的如《五燈會元》,也有區域性質的如《黔南會燈錄》。統而觀之,則可全面反映宗派史。
破山海明是明末中興禪宗的代表性人物之一,在西南地區影響深遠,于巴蜀禪宗史有重大影響,其后法嗣綿延四百余載,門人弟子輩出,支脈紛紜。隆蓮法師《書奉雙桂堂》“雙桂流芳遍兩川,千枝萬葉被西南。祖庭門戶欣重振,拄地撐天繼破山”,極稱破山法派之盛。今,雙桂門人釋身振以《錦江禪燈錄》、《黔南會燈》為本,輔以《五燈全書》,旁羅禪師語錄詩文,裒輯寺志塔銘,編著《雙桂禪燈錄》。自海明開山,迄于民國,近三百余年,凡十一世,五百六十六人。每錄一僧,先言其生平,既采《錦江》、《黔南》、語錄、師友贈答詩文、寺志。以記其言語,述其生平。
破山一脈雖宏盛西南數百年,而記錄西南禪史的燈錄卻僅《錦江禪燈錄》、《黔南會燈》、《五燈全書》之類,尤未及乾嘉之后,誠為可憾。咸同時,滇黔戰亂,是地佛教由此低迷,滇黔禪宗燈系亦遭支離,典籍著述散佚殆盡。莫友芝《黔詩紀略》卷首題記: “吾黔自軍興十余年以來,苗、回諸夷,土匪邪教,相繼倡亂,蹂躪全省十二府、一直隸州,……,殘破千里,人民能孑身脫難者百不一二,何問文獻!”故乾嘉以后滇黔燈系渺不可得。幸賴高僧輩出,著述宏富,故詩文《語錄》多有傳世。又有寺志傳今,碑文塔銘可補文獻之缺。故《雙桂禪燈錄》之編著,可補述前史而續綴后支,通連今古,以完其宗門法脈,并彌西南禪宗燈系之缺。
唐宋以后,文人大量參與到禪門說法中來,使不立文字的禪法演化成文字禪。明末清初之際,亦有大量文人逃禪問道,或門外談禪,或薙染出家。擴大了禪門影響,使禪法更具文字化、義理化傾向。《雙桂》所載禪師語錄多為五七言詩體,或四六對句韻文。或通俗或古奧。雖言文字,而實則本于“不立文字”,即所謂“借言以顯無言,然言中無言之趣,妙至幽玄”(《石門文字禪》)。通過取消理性邏輯的語言來闡發禪理,感悟佛法。通過指東道西、隱語雙關,乃至棒喝交馳來消解禪理對文字的依賴,從而使學人用內心去領悟超越種種對立的真實。
如學人問“佛祖西來意”,月宗印星言“星河忽發怒,梁山飛半空”,即以違背現實常理,以體悟禪理的超越性。善權達位言“翠竹黃花,便是祖師西來大意”,虛峨大照言“核桃一把抓”,則舉平常物,“青青翠竹,盡是法身;郁郁黃花,無非般若”,于平常背后,有弦外之音,而學人則需發現平常背后朦朧的禪機。這也是今天教外人閱讀禪燈的重要所在。使人的有限眼界拓展到無窮精神境界,啟心靈,增智慧。參悟燈錄,靖息時下浮說,還原禪法本真,功德大焉。
唯所采各燈錄記載有重,兼而錄之,未審刪汰,是其所病。雖延及民國,而仍集中于明末至乾嘉,是亦有待于更多文獻的發現與整理。而這似也合“不全”之理,文不全乃成全法,是其所謂。
(劉超)
書名:雙桂禪燈錄
定價:280.00元
作者:釋身振
